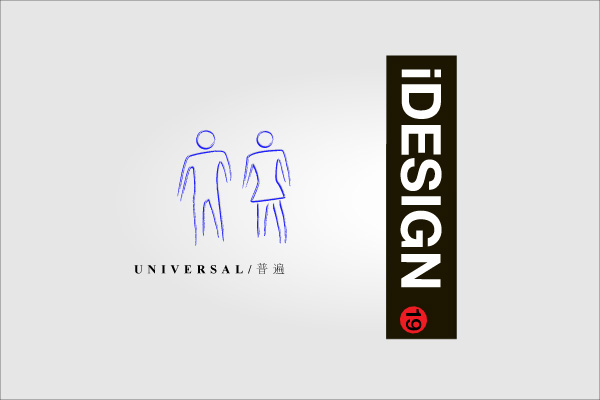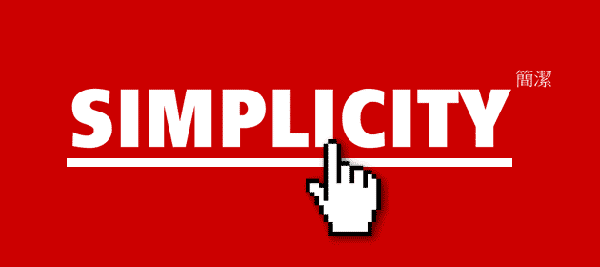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
这是UCDChina提前预览网页留下的存档,不包括作者可能更新过的内容。 推荐您进入文章源地址阅读和发布评论:http://www.hi-id.com/?p=2450 |
||
|
封面: 谈设计或者做设计,“创新”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词语,“创新”是“设计”存在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个“创新”是广义的。 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其他一些后继的必要条件,成为一个“设计”或者“好设计”,一般也不能称忘记,因为这些后继必要条件一般情况下都是混沌的,不像“创新”这个必要条件那样鲜明有形而有号召力,所以忘记可能是忽视或者意识不强,因为“创新”太有吸引力了。 那么这些易被忽视的设计的必要条件有什么呢?如果我们专说“工业设计”的话,有一个就是——“批量化”。“批量化”是工业设计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是写在“工业设计”的出生证明上的,“1980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给工业设计更新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维基百科上对工业设计这个词的解释,当然这个 ICSID 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前后有变化,最新的定义就没有“批量”。因为设计改变了,或许80年的那个定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工业设计”,与大批量、工厂的流水线等相联系,工业设计就是诞生于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工业设计是否不再有“批量化”的要求了吗? 看起来是如此的,因为在连“个性化”这个词在我们看来都是过时的时代来说,“批量化”这个词带给人的感觉就如同标准件,或者更甚,螺丝螺帽法兰盘,我们不再喜欢这个词语了,对它有一种感情上的抵触,因为这个词约略看上去是和“创新”或者“个性化”抵触的。而实际上,“批量化”并没有多少变化,作为设计师来说,更希望自己的设计不断“批量化”,iPhone 至今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万部。当然设计确实在改变着,不追求“批量化”的各种设计也不断出现,在作着各种不同的细分。 “批量化”这个词或许我们容易将其向“产量”上理解,比如一说起这个词,就会出现产品在流水线上行进的图像,这样随着设计不断发展,对设计师来说它确实越来越不值得关注,因为“产量”在设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是一件容易控制的事,也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是不会被“产量”这个因素所牵制的,生产一件生产一万件的设计可以是同一个。 但是我们忽视了另外一面,“批量化”的生产来自于“批量化”的需求,即无论设计怎么改变,它始终要面对的是消费者,而这个消费者无论人数的多少,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众”。无论是80年代说的“批量化”还是现在说的其他词语,始终没有改变的就是设计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只不过80年代的设计类似于供方市场,与消费者有着较远的距离,所以“批量化”这个词就更集中在生产制造上,而现在我们将关心的中心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仍然是一个“批量化”。始终没变的就是“大众”,无论是大批量如 iPhone 这样的产品,还是针对专门消费群体的小批量产品,甚至是单件产品都无法躲避这个大众,因为即使如单件产品,比如某一人的室内设计,我们依然无法忽略“大众”的存在。不过在设计中我们很容易忽视消费者的批量化属性,甚至会将消费者具体起来,像一个与自己心有灵犀的朋友。 我们在对设计的目标消费者理解上喜欢这样做,喜欢将其活生生的刻画出来,在设计提案中也喜欢将他们具体化,比如赋以性格之类,因为这更利于讲故事,可危险的是在设计开始或者设计之中也是这样做,就是将目标消费者具体化,忽视“批量化”的一面。因为大众不仅很抽象,而且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实在太大了,也许我们将大众具体化为某人(许多时候是“我”)更容易我们理解与交流,或者局限在受访的调研人群上,我们并不否认大众的存在,而是这种缺乏对“一般性”的探求而就近就方便就直接理解而对“大众”作了片面的认识,当满怀信心期待“花见花开人见人爱”到来时,等来的却是一些疑惑,“为什么他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识不到这个设计的价值,为什么这么富有创新的东西对他们就没有吸引力……” 我们到处可见这些“自以为是”的创新,比如我们前一篇说到的 Nook,更前一点的 Courier,都能发现这些影子,等等。它们身上的创新是不可否认的,比如 Courier 的那种拖拽的设计(将需要拖拽的图标拉到中间,就像别针一样别在上面),有的单独来看是非常吸引人的,比如你带着 Nook 去 Barnes & Noble 的实体书店中使用Wi-Fi网络可以免费阅读书,看上去结合了先进科技和旧式生活的质感,但是设计不只是单靠这些“创新”可以支撑起来的。 设计不仅需要通过自己的认可,需要通过甲的认可,乙的赞赏,丙的喜欢,丁的褒奖……需要面对的是整个目标消费群,而甲和乙不是同一人,在同一个产品上丙和丁又有太多的不同认识,我们如何去满足每一个人?或许开天辟地的“创新”能够满足每一个人,就像 iPhone,但事实却不是这样,iPhone 并没有开天辟地的“创新”(这一点我们在 iPhone 发布那一天就说了),如果严格一点说,所谓的一呼百应的开天辟地的“创新”是不存在的,尤其在产品设计上,它与消费者的接触不是点到点的,比如碰一个头就行了,而是有历程,设计也不是“点子”,而是“创新”的物化应用,需要酿造。 为了便于理解和交流,有时我们需要将“大众”具体化,甚至具体化成个体,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将“大众”的一般性即我们所要面对的大众的共同性进行探索和抽象,亦即“普遍性”。 设计需要面对大众,需要满足大众的潜在需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潜在的需求并不是都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也是“发现”作为设计师基本能力的重要所在。当我们去问客户或者消费者他们“需要什么”的问题时,多数是没有答案的,反而对方如果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并不能只依靠于对方的语言表面意思。而且更复杂的是,我们探索的那个大众的“普遍性”并不只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上下文背景。 Universal 这个词我们经常会见到,比如说人类共通的情感,不仅甲乙丙丁都有,在设计师自身身上也有,每一个人的喜好都能够代表起很多人的喜好,但是很多人的喜好并不一定是大众的喜好,也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普遍性”,所以当我们以自己作为对象的时候,尤其需要跳出一个分身来审视和疑问,而且我们需要将这些特征进行抽象,而不是“我喜欢什么”就满足你的喜欢。如果有足够的把握,即从大众中抽象到“普遍性”的能力,那么即使没有实质化的大众代表也无所谓,就像有的公司比如 Apple 之类反对的焦点小组。 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直接的可以剔除设计中一些“自以为是”的创新,这个“自以为是”不是指个性诸如个人风格等,而是那种将个人喜好直接代表大众喜好的东西(生活中也是,谁也不希望被胡乱代表)。创新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经过一定训练的人都可以天马行空一番,甚至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创意,也可以说人人都可以是设计师。但创新并不能成就一个设计,尤其是一个面向他人的设计,当创新没有进入应用的场景,那么它就只是点子,如果生生将点子拧成设计,就会变成“花俏”。 那么在普遍性上作过探索的设计是不“花俏”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这也牵涉到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一个主题,就是“标准美”,比如这篇文章的评论部分以及论坛上的一个讨论。我们可以从一些对比中来认识一下“Universal/普遍”。 iPhone 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因为现在与之可以比较的手机已经很多,比如 Android、Palm 等等,我们可以尝试先抛弃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比较一下这些手机的界面设计,哪一个会更受人们喜欢?哪一个最花俏?哪一个最像一种标准?……我想 iPhone 最具标准美,所谓标准就是人们默认的一个东西,在一般情况下它有作为中心参考的唯一性,它上面没有太多修饰和补充,这就是我们说的“普遍性”的认同,比如 iPhone 没有像 Palm Pre 主要界面的圆角处理,没有 Android 抽屉式的推拉操作。最好的例子就是三个手机解锁操作的设计,哪一个更能获得“普遍性”的认可?是否我们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背景条件下,设计也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规则?而这条直线就是标准,就是“普遍性”的基准,而它并非都是被先行者给抢到的,因为这条线不是事先可以描述的。我们还是可以用三个手机解锁界面操作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这三个操作界面放在一起,任意拿掉一个(假设它不存在),但是它必将会再次出现(比如另外的设计师设计出),也许很快出现,只不过细节不同而已,那么会是哪一个呢?这就是“不可避免”-inevitable。 inevitable 这个词 Apple 的 Jonathan Ive 说过很多,比如在 Objectified 中他说到:
在 Who Is Jonathan Ive? 中页说到过:
Naoto Fukasawa 也说到过几次,比如在 Wallpaper 的访谈中他描述自己作品的三个词语就是“Complete, inevitable, normal. ”与之相关的可以和他的原型说(archetype)联系起来。 inevitable (不可避免或者必然) 并不是说一种抢标,比如如果 iPhone 的屏幕解锁界面如果没有设计成现在那样,就一定会有后来者设计成如此一模一样的,而是在一定的外在环境之下(时间,科技,市场之类),我们所追求的最佳的这个目标会类似一个凝聚状态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就是“普遍性”决定的,当然如果你认为设计没有核心,只有不同的平等的选择,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成立。 而去认识我们所要面对的大众,尤其是探索认识他们的“普遍性”是不可避免和不可忽视的,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个体的“特殊性”所吸引住了。 《iDESIGN 19》
原研哉关于日本的简洁 纽约时报委托“iA”对原研哉(Kenya Hara)作一个访谈,关于日本美学,想知道是否日本的所有东西的设计都和他们漂亮的便当盒一样(bento boxes),“iA” 上贴了原研哉回答的日文和英文版。 纽约时报问道为什么日本看上去对美有更高的鉴赏力?日本人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看重美的构成和体验?在日本是不是一般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设计过的?原研哉回答从他对东京机场的体验开始,他觉得东京的机场非常糟糕,但是它很干净整洁,地板都是深深擦亮过的,日本人对清洁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审美力,日本的工匠精神( shokunin kishitsu)深深植入了每一个行业(街道建筑工、电工、厨师等),一只日本的清洁队会在他们勤勉的工作中找到满足。原研哉认为就是工匠精神感染了人们的审美意识,比如精心、细致、细心、简洁。欧洲也有工匠精神,只不过他们是到达一定程度的(专业),而日本则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比如清洁和烹饪之中也是如此。日本人以独特的审美意识著称,但是他们同时对丑陋没有相称的认识力,因为总是专注于美的东西而忽略丑的,所以可以看到日本不相称的很糟糕的杂乱建筑,可以看到一位日本工人在陈旧的会议室或者拥挤的人行道上打开精美的便当盒。 纽约时报问道是否一般的东西在日本都是经过很好的设计的?原研哉说日本的一个中心美学原则是简洁,但是日本的简洁和西方的简洁不同,他以上面两把刀来作为对比的例子,德国的 Henckel 刀非常容易使用,因为人机工程的设计,拿起刀拇指就会自然地找到合适的位置,而日本的厨师不喜欢有人机工程的设计,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技能,当然它并不是粗制滥造,相反,完美的平坦设计似乎对厨师说你可以找到符合你的技能的无论那一个位置。超越花哨的美是日本人知觉中最基础的美学原则。
Motorola Droid 和 Android 2.0 Motorola 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手机 Droid 推出了,首个周末就售出了10万台,但这远远还未达到朝天阙的量级。尽管很多人都讨厌来一台新的所谓智能机动不动就试问是否 iPhone Killer,但如果说现在一个公司推出一部新机而说不关心 iPhone 到底怎样我只是走自己的路,这样的愚蠢是无法想象的,无论如何4000多万部 iPhone 都会挡在前面。挑战 iPhone 似乎必须跨过一条境界“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尤其“似我者死”这一条,那么求生只有一条,努力从 iPhone 中寻求差异化,尤其是在设计层面,用户能够感受到的一面,如果能从 iPhone 的差异化中鲜明的凸显出来,而且有很好的执行(即为了差异化什么都管了,那就不是设计而是娇嗔),其实这看起来并不是很难,就好比 Zune HD,Solid 是非常切中要害的词。 Motorola Droid 也在 Solid 上表现出了它的追求,直棱直角,只不过本来更加直棱直角,这台机子的首个运营商 Verizon 认为这样太男性化,Motorola 就马上磨圆了边缘,并且在背部加上了橡胶,纽约时报的报道。Droid 整机也做的很紧凑,而且为了不陷入窠臼,下巴的设计比较能突出这种诉求(否则就没有自己独特的外在形象了)。从目前也就是首批消费者来看,人们非常满意,这并不说明 Droid 的设计非常优秀,而是人们有这种差异化的期待,当然对 Motorola 也有一种期待,只是还不够非常不够。这是一部有着明星家底但没有明星气质的手机。Droid 的评测可以见 Engadget 和 Gizmodo 。 与之相比,搭载在 Droid 的新系统 Android 2.0 就带来了更多的惊喜,Droid 是首部应用 Android 2.0 的手机,所以这也是 Droid 受欢迎的一个原因。Android 2.0 有很多的更新,当然作为来自 Google 的手机系统,最重要的是它会是 Google 原生程序的首个应用场所,移动设备最重要的是应用尤其是互联网应用,而开发这些应用最厉害除了 Google 还有谁?Android 2.0 上最具号召力的应用就是 Google Maps Navigation,视频介绍见此(youtube),地理(地图)移动应用也是移动设备最重要的,而这方面除了 Google 就没有谁了。Android 2.0 的视频介绍可以见这(youtube),界面有很多新的设计,比如图标相比 Apple 更干净更小,也比以前的更精炼,更多 Google 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你的“阅读”改变了吗?关于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 人们已经不再读书了,但人们比以前有更多阅读了,那么你的阅读是否有变化了呢,尤其是屏幕阅读带来的改变,详细的讨论见 iDESIGN ,下面摘取几段:
……
|